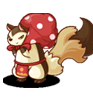我是哈克。
我现在站在橙黄色的麦田里,有阳光照在我身上,我很满足。
直到我看见她。
她从麦田的另一头走过来,穿着漂亮的格子衫。那件衣服的花纹我很喜欢,因为它和我身上的这件勉强能算是衣服的布匹上的纹案一模一样。
这时候有两只可恶的麻雀站在我的帽子上啄褶皱里的草籽,我想我现在的样子一定失态极了。我想扭过头去保留一点点脸面,可惜脖子的材料太过僵硬,让我只能挺着脖子窘迫的面对着她。
但是她似乎没有介意,只是继续向我走过来。她的眼睛很美,有着湛蓝的颜色,好像倒映着整个天空。她背对着阳光站在我面前,可我只能看清她漂亮的蓝眼睛和模糊的轮廓。
我看见她轻轻歪着头看我,我想也许她现在的神情是认真而专注的,也可能是笑着在研究我滑稽的红鼻子。那个歪歪扭扭的鼻子挂在我的脸上确实不协调,我能看到它得益于我的主人,他曾贴心的用镜子摆在我面前,让我得以看见我自己的滑稽摸样。
然后我听见一声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呼唤声,我想那声音因该来自一位母亲。那声呼唤被风拉的很长,让我听不清是什么意思。
但是她似乎听懂了,望了望声音传来的方向,然后向后退了几步,让我终于能看清她的容貌。但我还没来得及细细端详,就听见她的声音:“喂,我要回家了。”
这么快吗?但是我无法问出声音。我也忘了要问她什么,只觉得她的声音是那般的好听,就连说一句“喂”也像是在唱一首歌。
她转过身,面向天的那边巨大的夕阳,我才意识到原来已经是黄昏了。我看着她在麦田里飞快的跑远,脚步轻快,发出一连串的响声。那声音敲击在我的心底,望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莫名的开始厌烦日复一日站在这片麦田中的日子,第一次对自己稻草做的身体产生了厌恶。
我的心里只重复着一句话:我想要奔跑。
从那天之后她开始频繁的来到我的面前,但是很少说话,有时在我旁边一坐就是一整天。但更多的时候她是迎着风在麦田里奔跑,似乎从不疲倦。锋利的麦芒割破了她的格子衫,割破了她娇嫩的皮肤,而她并不理会,只是沉浸在奔跑的欢愉中,好像是遗忘了整个世界。
我多想牵起她的手对她倾诉我的愉快与悲伤,我多想和她一起奔跑,在夕阳下在麦田里留下我们的步伐。那样的日子反复出现在我的心里,刻印在我的脑海里,像一场美的有些迷离的梦。
但是我却怎样也无法实现那样的奢望,我根本无法用自己的身体迈出一个步子,我只能在原地站着,一点点随着她奔跑的步伐将自己的身体恨进了骨里。
这个下午她又一次来到了我的身旁,却和往常并不一样。她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我面前,又一步一步的从我面前走到很远的地方。她是数着步子走的,在数了第一百下的地方她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面向着我。
她又开始奔跑。这是她第一次面对着我奔跑,风吹起她的长卷发,似乎在她身后展开了一双巨大的翅膀。她跑到我面前,我看到她笑的一脸落寂。
她在我面前展开双手,模仿着我的姿势。我曾经一直觉的那个姿势美极了,像是要拥抱什么。但她看起来却悲伤极了,声音有些冰凉。
“你看,我和你一样。”
“一样的帽子,一样的衣服,一样的动作。”
“可是哈克,你能和我一起奔跑吗?”
我愣在原地,甚至没有察觉到她的离开。
我想我要离开这里。
这是在她消失的十天后我做出的决定。
看不见她的日子让我几乎癫狂,可我却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,这感觉真是太折磨人了。而这样的悲伤是连我最爱的阳光也无法抚平的,因为我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她奔跑的身影已经印在了我的灵魂最深处。
但是我实在无法自由操控我僵硬的身体,只能够笨拙的晃动几下。但是我知道如果坚持不停的晃动也许有希望从土里脱离出来,因为我曾经看到一根被***土里的木杆,经过一下午的挣扎而离开了土地,被人拾去了。
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人拾去,或者我可能会倒在地上,只能任白蚁啃噬我的身躯。不过也许它们并不屑啃食那些枯脆的稻草,而是更青睐于腐朽的树木。
最终我的下场也许只是在泥土里腐朽衰亡,而我觉得不因该放弃希望。我加大了摇晃的力度,刚好有一阵风吹过来,于是——我成功了——也许更像是失败。
我向后倒去。我还是没能控制好方向。我感到了那些组成我身体的稻草都散开了,而只剩下一副木制的衰朽了的骨架。视线涣散的前一秒,我看见了她湖蓝色的眼睛,那里面倒映着无尽的麦田和奔跑着的我。
我是一根稻草。
据说我曾经是一个稻草人身上的一部分,但那个家伙没有珍惜我,才让我从他的身上离开。
我现在躺在橙黄色的麦田里,有阳光照在我身上,我很满足。